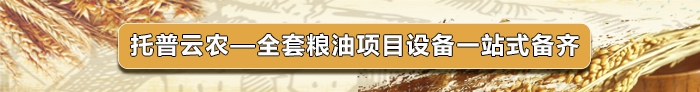粮食安全中政策方面的若干问题
一、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不完善,财政的负担加重、效率下降
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调动农民生产粮食积极性的作用显而易见,但由此造成的高额财政成本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东部某省一主产县(市)的调查显示:2005年,在当地财政支持下,该市国有粮食企业按每公斤1、33元的价格托市收购小麦,却遭受每公斤小麦亏损0、09元的损失;收购价和保管费相加后每公斤粳稻的收购成本为2、0元,亏0、24元;其他稻谷每公斤亏损0、2元;全年该市总亏损2000万元。而2006年小麦由中央储备粮管理总公司收购,地方财政不承担亏损责任,若出现亏损,则由中央财政承担。目前,该省遗留的粮食政策性亏损挂账还高达100多亿元。该省4家被调研的企业中有3家认为,2006年的托市收购将造成新一轮亏损挂账。据该省有关部门反映,该省的一些农民因价高将本来储在家中的粮食也卖给了国家,更加重了财政负担。
政府之所以选择并坚持现行最低收购价政策,除了价格支持政策在稳定粮食生产、确保粮食安全方面比较有力之外,关键在于政府在政策选择方面存在路径依赖现象。直接将加入世贸组织之前实行的粮食保护价收购政策加以改造,沿用既有的国有粮食企业收购渠道,主要采取限定时间、划定区域、放开收购等边际性创新措施,转换为最低收购价政策,这种制度创新的净收益高。尽管现行最低收购价政策加重了财政负担,增加了制度运行成本,但制度创新的净收益仍然大于零,故该项政策在一定时间内仍可能延续。
二、粮食储备规模过高,财政支出过多
中国农民有着传统的自种口粮及自储粮食的习惯,因此,占人口总数近60%的农民的粮食安全是有保障的。按照国际公认的储备粮占全年消费量17%~18%的粮食安全储备标准,中国对非农业人口的粮食安全储备约为350亿公斤,加上国内正常粮食缺口250亿公斤左右,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总储备规模应为600亿公斤左右。但是,2001~2005年,中国的中央和地方粮食储备规模大多高于应储规模1/4以上,2005年更是高达2/3以上。按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粮食安全储备标准及2010年、2020年的国内粮食消费量预测,中央和地方粮食储备规模分别应为880亿~930亿公斤、960亿~1000亿公斤,即使考虑大国效应和中国粮食市场有待完善,适当提高储备率,也比有关部门确定的中国2010年和2020年的粮食安全储备目标低不少。由此可见,中长期中国的粮食安全目标定得过高,将给今后国家财政增加不必要的沉重负担。
粮食储备规模之所以过高,一方面,是因为受到粮食市场并未完全统一、现代粮食物流体系尚未形成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因为还存在一些涉粮企业和部门构成的利益“小集团”,其影响粮食储备政策的集体行动能力远高于原子型的广大纳税人以及一些由非粮食部门组成的“大集团”,致使粮食储备资源的配置难以趋向帕累托最优状态。
三、储备粮分级管理体制存在缺陷
中央、地方分级粮食储备制度,其实是延续过去的制度安排。20世纪90年代初之所以要出台分级安排的粮食储备制度,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与当时中国粮食市场发育很不充分,地区之间尚未真正建立起统一、开放的粮食市场体系有很大的关系;二是当时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很低,中央不愿意独立承担调控全国粮食市场的责任。但是,目前情况变化很大,继续沿用中央和地方分级储备粮食的制度,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容易削弱粮食储备的调控能力,使其本应发挥的作用大打折扣。一方面,在全国粮食市场统一的情况下,短缺或“卖粮难”都将是全国性现象,不会限于局部地区,这种制度安排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每个区域内同时设有中央储备粮和地方储备粮,必然会发生利益矛盾,影响储备粮调控作用的充分发挥。当粮食供不应求时,地方政府考虑的不是抛售地方储备粮以平抑市场,而是为了确保地方粮食安全增加或补充地方储备粮,加剧了粮食市场的紧张;而当粮食供大于求时,地方政府为了减少自身的财政支出,考虑的是尽可能多地增加中央储备粮。例如,1993~1995年,中国粮食市场呈现紧张局面,尽管国家动用储备粮以支持粮食部门挂牌限价销售,但许多地方却在这个时候出台建立和充实地方粮食储备的政策,例如,江苏省在1993年底为贯彻国家平抑市场粮油价格的决定,提出要“充实储备,凡是储备不足或没有到位的,要迅速采取补救措施”。而1996年后,粮食过剩,需要加强粮食储备时,地方却又不积极,纷纷要求中央来收购。地方粮食储备的这些逆向操作行为,不但不能发挥好粮食储备的调控作用,反而会影响中央储备粮的调控效果(王健,2004)。2003~2004年,再度发生中央和地方的逆向调控行为。在市场粮价开始不断上涨之时,中央政府设法运用多种手段稳定粮价,而地方政府不但不平抑价格,反而趁核实粮食仓储之机抓紧补库,实际上对市场粮价起到了抱薪救火的作用,加剧了粮食市场的波动。
粮食市场之所以出现中央政策和地方政府的逆向调控现象,主要是因为双方追求的政策目标不同,彼此的效用函数差异较大。从政府角度来看,粮食安全主要表现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有的全国性公共产品。在“分灶吃饭”的财税体制下,中央政府出于维护国家主权独立、保持社会稳定的政治考虑,抓粮食安全的动力足、主动性强。地方政府从政治上通过“粮食省长负责制”的委托—代理链条,接受中央政府委托来抓粮食安全,动力小、消极被动。地方政府从某种程度上也属于“经济人”,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追求地方财政收入最大化,抓粮食安全不仅难以增加财政收入,而且加大了财政支出。当一个地区粮食安全有了保障之后,若再扩大粮食生产和储备,只能增加其他地区居民的粮食安全效用,财政支出却要由当地政府替中央政府或其他地区政府承担,这种让某个地方政府长期为国家做贡献的“捐赠式”政策安排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在现行粮食政策和政治体制下,当粮食市场过剩或短缺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博弈的结果就是逆向调控。
四、储备粮代储制度不规范,国有粮食企业储备效率低下
中国储备粮的代储制度很不完善。目前,中央直属储备库直接管理的中央储备粮只有30%左右,70%左右的中央储备粮都由地方粮库代管。但是,地方粮库代管中央储备粮存在着两个比较明显的问题:一是委托—代理关系不规范;二是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当代理人的利己动机和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同时存在时,就会在两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中产生非协作、低效率的问题。中国当前的中央储备粮代储问题也是如此,大多数代储库没有经过严格的资格认定,代储中央储备粮时不是通过公开招标的形式进行的。由此造成了信息不对称,中央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对代储库的资产、财务状况和承储条件不太了解,致使有些储备粮装在交通不便、设施较差的粮库,有些甚至装在管理水平较低的临时收储仓库。前几年连续发生的几起代储库储备粮亏库,或未经批准销售储备粮,甚至动用储备粮炒期货等事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方代储库未经良好的考察和认定,以及没有严格的制度约束等问题。
本课题组2006年在东部某主产省调研时,一家大型民营企业表示,民营企业参与国家粮食储备,仅靠财政的储备补贴就能赚钱,而且只要按现行国家储备粮补贴的八折标准获得补贴,就愿意自建粮库专门从事国家粮食储备。某市粮食局的一位干部也认为,民营企业只要得到国家储备粮补贴的八折甚至更低,就能为国家建仓储粮。低成本的原因在于民营粮食企业比国有粮食企业储备效率高。